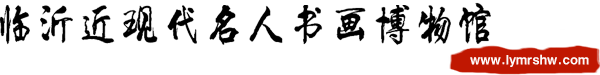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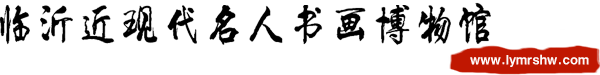
| 风范—怀念张寿民先生 |
|
发表时间:2014/11/19 来源:临沂近现代名人书画博物馆 |
| 得知张寿民先生逝世的消息时,我正在开会,未能去医院最后见他一面,深为遗憾。 寿民老是我的领导和尊长,彼此交往十分密切,又有过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。我与他相知相交的岁月,正是他人生的低谷时期和生命的迟暮时分,对他的了解,就有了某些独特之处。 1965年,我刚到临沂师范学校时,他任师范学校的校长。有一次,我为学生讲课,见一位老者坐在藤椅里认真地听。老师们告诉我,这位与鲁迅面目相似的老人就是张校长,我与他就这样认识了。那一年,他57岁,正是我现在的年纪。 八个月后,“文革”开始。当时已经调任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主任的张寿民先生,被打成“黑帮”羁押到师范学校。在全国批判“三家村”的同时,他成为临沂“文革”中第一批受害者。说来奇怪,我当时属于既非“革命动力”亦非“革命对象”的中不溜儿,在批判他时,从未有人要我置喙,我成了一个旁观者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急风险浪,张寿民先生显得从容沉稳,对于那些尖刻的言辞、过分的举动,他始终保持着平静,甚至还在批判间隙摸出冷馒头旁若无人独自充饥。有一次正在批判他,他声言要去厕所。也许是他老了,大家认为他不会跑,所以他去厕所时没有人跟踪。谁知他一去不返,有人让我去看看,我出去一看,不禁捧腹。原来,他正同一群小孩捏泥制品。我第一次发现,他那双苍老的手居然那么灵巧。从此之后,他的室友都有他赠送的泥制品,或笔筒,或花盆。我虽与他毗邻而住,也得到一只张氏笔筒。他的豁达,他的乐观,于此可见一斑。 在两派争斗的日子里,对他的监管比先前松了一些,许多教师走出了“牛棚”,但他还在劳动。有一件事,我印象尤深。当时,师范学校的校园里有个水塘,水塘的低堰上种着几棵柳树。因为无人管理,其中有一株已经倒伏,且根须外露。后来,我发现这株柳树竟然奇迹般地挺立起来了。潘国栋老师告诉我,张寿民先生经常为这株柳树培土,是他一锨一锨从北塘边上挖来土救活了它。我仿佛看到了熹微的晨光中,一位身处逆境的老人,迈着蹒跚的步履,为救活一棵树而辛苦劳作。从那时起,我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。 70年代初期,我从“学习班”出来后,奉命与他一起办一个小卖部。我负责进货,他则管售货,在他漫长的一生中,就有了这一段短暂的“老板”生涯。此时,我们同心协力,相濡以沫,相处十分融洽。每当向人介绍我时,他总是以一个忠厚长者的身分告诉大家:钱老师的爸爸是一个革命干部。其实,那时候我父亲早已含冤身亡。有一次我问他:你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吗?他点点头,说:“要相信历史。”于是,我十分感激他。 此后约半年,我被再次下放,两年后重返临沂。其时,张寿民先生住在第一小学。每年农历初三,我总要去拜望老人家,这是我最舒心的日子。我们共处一室,相对而坐,海阔天空,尽情而谈。当暮色降临时,他的夫人早为我俩准备了晚餐。我们边饮酒边聊,直到夜深人静,才恋恋不舍地分手。 岁月匆匆。张寿民先生毕竟长我33岁,年岁不饶人,他的身体每况愈下,也时常去住医院。但当他精神好转时,我们还是在他书房里神聊。谈历史,谈周易,谈文学,谈世界上发生的大事,唯独不谈他的过去,他的坎坷,更不提往日的荣耀。我多少有点惊讶,有一次问及此事时,他淡然一笑,说:“连刘少奇都到了那种地步,我还不是很幸运?”这种大度,这种坦荡,我深为感动。还有,谈话凡涉及某位人物时,他从不贬抑,即使是曾经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人,他总能举出人家的许多优点。这使我想起师范学校的教师们在“文革”中对他的评价:张寿民真是一个毫无防人之心的好人。他的这种道德情操令人折服。 张寿民先生是全国知名的书法家,他的书法雄健遒劲、俊逸流畅,自成一体。就是武中奇、欧阳中石等书法大家也对他十分敬重。全国各地慕名求墨宝者络绎不绝,他只好挥笔不止。我因虑及他年事已高,从未向他索要过一幅字。谁料,他让他女儿张惠珍送来了一副专为我题写的中堂,上书”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“,我受之有愧,把其视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尊长对自己的勉励。 危难之中识英雄,细微之处见精神。在我与张寿民先生长达30余年的交往中,因为年龄的悬殊,未见其雄姿英发、叱咤风云的一面,甚至也未见其一校之长的风采,而是一位长者与一个后辈在特殊的年代结成的一种特殊的情谊。他那处变不惊的气度、老而弥坚的勤奋、平易近人的作风、宽厚待人的情怀,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风范,是他的人格力量在一个侧面的显现,他的崇高品质,永远值得我们缅怀!(钱勤来) 原载《临沂日报》1998年9月14日 |